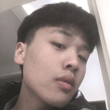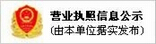界面新闻记者 | 徐鲁青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1860年中英签订《北京条约》时,英国随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把摄影机架在礼部大门前,打算记录下历史时刻。时任礼部主事刘毓楠回忆此事,在日记中写到,“至礼部大堂檐外设一架,上有方木盒,中有镜,覆以红毡,不知何物。”
和刘毓楠一样,大多数东亚人彼时对摄影机仍颇为陌生,没人知道这种奇怪的方木盒未来将出现在皇宫、照相馆与街头。《北京条约》签订那年,中国的东南沿海陆续出现了职业摄影师。两年后,出使清朝的朝鲜使团,在北京的“俄罗斯馆”拍摄了目前发现最早的朝鲜照片。海对岸的日本,长崎与横滨刚刚开业第一批照相馆,并迅速扩展至全国。
“错综的视线:早期摄影在东亚(1850年代-1919年)”展览日前在长沙谢子龙美术馆开幕,呈现了五百多幅19世纪后半期的东亚摄影作品,免费向市民开放。一部分照片来自最早一批拍摄东亚的欧美摄影师,有人随军队前来,有人以学者身份在东亚做田野,用镜头定格幻想的东方。还有一部分作品展现了东亚内部互相观看的影像,试图与西方凝视建立对话。无论是日本摄影师借征服之势拍下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影像,还是第一批掌握了摄影术的中国人拍摄自己,在拍照时,人们不仅只是按下快门,也在重新理解自身。

“错综的视线:早期摄影在东亚(1850年代-1919年)”
当枪炮与摄影镜头对准东亚
摄影机伴随着炮火与暴力进入东亚。费利斯·比托是最早拍摄东亚以及中国的摄影师之一。1860年,他跟随英法部队,从香港向北行驶至大连湾、北塘与海河河口的大沽炮台,接着又到了北京的颐和园。他记录了路途所见的北京景象,也随军拍下许多残酷的战争场景,包括英法联军攻占天津以及洗劫和烧毁北京皇家园林。

费利斯·比托《北京城城墙东面及其东北角》,1860年,蛋白印相,原作藏于谢子龙影像艺术馆

费利斯·比托《雍和宫》,1860年,蛋白印相,原作藏于谢子龙影像艺术馆
比托在大沽北堡角拍摄的照片是中国最早的战场尸骸影像。英国军事医师戴维·雷尼(david f. rennie)博士在回忆录中写道,比托来到这里后显得非常激动,因为觉得场景很“美”,并恳求在他的摄影完成前不要移动尸体的位置。

费利斯·比托《北塘炮台》,1860年,蛋白印相,原作藏于谢子龙影像艺术馆
摄像机在此时常常与枪炮构成隐喻关系。作为为数不多的随军摄影师,比托有机会接触并拍摄恭亲王奕䜣。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比托拿镜头对准恭亲王时,后者“惊恐起来,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以为他对面的这门样式怪异的大炮会随时把他的头给轰掉——那架相机的模样确实有点像一门上了膛的迫击炮,准备将炮弹射入这个可怜人的身体”。

费利斯·比托《恭亲王奕訢》,1860年,蛋白印相,原作藏于谢子龙影像艺术馆
1963年,比托离开中国,前往日本横滨开设了照相馆,制作并出售颇具异国情调的日本风景、风俗以及日本人肖像的相册,掀起了“横滨写真”风潮。横滨是日本最大的开埠城市,写真作为纪念品在外国游客间十分受欢迎。直到1887年,被称为珂罗版的摄影制版技术开始普及后,"横滨写真”才逐渐让位于更便宜的图片明信片和摄影集。

“横滨写真”展览图(图片来源:徐鲁青)
展览中呈现的另一位摄影师是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戴维·甘博。甘博从1917年开始,四次来到中国进行社会调查。由于器材的变化,他拍摄中国的方式与比托很不一样,他随身携带相机拍摄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朋友回忆甘博随时背着“笨重、难看的相机”,在沿途各种环境下冲洗底片;甘博也在一篇日记中提到,为了冲洗照片,他的水壶装了十七次水。

西德尼·戴维·甘博《甘博父子三人在街上拍照》,1908年,浙江杭州,原作藏于杜克大学鲁宾斯坦图书馆

西德尼·戴维·甘博《岸边露天的剃头铺》,1917年,湖北宜昌,原作藏于杜克大学鲁宾斯坦图书馆

西德尼·戴维·甘博《担柴禾的人》,1914年,四川绵阳,原作藏于杜克大学鲁宾斯坦图书馆
另一方面,镜头还迎合了西方人对东亚性别化的窥视。在展览开幕当天的学术论坛中,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吴盛青提到了一个欧美摄影师在中国的拍摄笔记。1880年左右,摄影师收到一位广州大户人家的邀请,要他给先生的家眷拍照,但要求不可以看见家眷。摄影师到达后发现客厅里拉了一个帷幕,剪开了一个洞,镜头从洞中穿过,他就这样拍下了家眷的照片。吴盛青久久忘不了这个故事,她感叹,“此时的摄影术不仅属于文化的霸权,也是性别霸权的结果。中国的男性对于女性的看见和不被看见拥有控制的权利。”
吴盛青还谈到,西方摄影师进入日本后拍摄了许多相对私密的女性照片,比如沐浴、抚镜自照等。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人对上半身的理解是脸部的延伸,而非西方理解的具有性意味的身体,乳房和胸部的袒露并不奇怪。欧美摄影师则将这些照片拍下来,回国作为情色写真售卖。她认为,除了作为枪炮的隐喻,镜头也如同阳具,成为撩拨与情色想象的工具。

方苏雅《云南厘金局局长夫人及孩子》,1899年,手工上色玻璃幻灯片,原作藏于谢子龙影像艺术馆
方苏雅室一位法国外交家、摄影师。1899年10月,42岁的他带着7部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历时11个月后终于抵达了当时的云南府城昆明,在此后的近5年时间里,他拍摄了云南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等,还曾用镜头完整记录了滇越铁路的修建过程。他还拍摄了长达一个小时的电影片段,堪称最早最完整的记录下晚清帝国图景的纪实性影像电影。
东亚内部的交错视线
“不要把最早期的摄影简单化,认为只是帝国主义在坚船利炮下的单向观看,东亚内部相互之间也有观看的兴趣。”策展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提醒观众。
19世纪后半叶,除了比托与甘博一众欧美摄影师,东亚不同地区也存在互相的拍摄,占很大比重的是日本人去到中国与朝鲜半岛记录当时当地的场景,比如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和藏学家青木文教。后者曾受日本寺庙派遣到西藏留学,他住在拉萨的民居里,记录了西藏的生活。
在朝鲜半岛,摄影术最早的传播更是和中国紧密相连。1862年,出使清朝的朝鲜使团在北京的“俄罗斯馆”拍摄了目前发现的最早朝鲜照片。直到19世纪80年代,朝鲜人主动拍摄的照片几乎都摄于北京。

青木文教《拉萨市街》,1912-1916年,图片来源于广东美术馆

青木文教《西藏的戏剧》,1912-1916年,图片来源于广东美术馆

青木文教《遥望布达拉宫》,1912-1916年,图片来源于广东美术馆
摄影术逐渐传入中国则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从东南沿海扩散至北方。在最早一批拿起相机的中国人中,黎芳被认为最重要的一位。1859年,他创立了自己的照相馆“华芳映相楼”,位于香港皇后大道,是中国香港地区最早期的照相馆之一,曾为李鸿章等政务要员拍照。
1879年秋,驻北京的几位外国公使邀请黎芳去往北京为其拍照。他带着摄影器材一路“旅拍”,拍摄了近百张照片。回港后,他把照片制作成《北京及周边摄影集》,向来旅行的西方人销售。

黎芳《广州大员坐像》,蛋白印相,图片来源于广东美术馆

黎芳《广州药房街》,1870年代,蛋白印相,原作藏于谢子龙影像艺术馆
“凝视”作为经典的摄影理论,东方主义是无法避开的理论视角,展览或许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凝视展开新的思考。“交错的视线:东亚内部的自审与互视”部分可贵地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东亚各国的互看影像,但许多问题有待探索,比如:东亚内部的视线与西方凝视构成了何种关系?呈现出什么样的异同?它们如何互相影响、形塑、对话?展览中景观与人像照片皆有呈现,但彼此之间的联系稍显断裂,它们的关系是什么?如何阐释彼此间的勾连?这些或许是在试图构建早期东亚摄影脉络时可以更进一步延展的问题。
参考资料: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1819779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30560.html
http://www.zgmsbweb.com/home/index/detail/relaid/20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