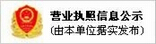2021年,富士停产多款胶卷,市场上流通的现有胶卷大量减少。一卷胶卷三十六张,从五六年前十元一卷,到现在七十到一百一卷,几年间价格疯涨,年年翻倍。
即便如此,仍有人执着地爱着它。“胶片不死”嵌入了他们的生活状态,不止那些摄影“老炮”,也有90后、00后闯入胶片爱好者的行列,寻找着一种延迟满足和随性自由的热爱。
胶片已死?
数码摄影时代,胶片产业日渐式微,很多人对胶片产业的未来表示悲观,甚至一度出现了“胶片已死”的讨论。
“胶片摄影当然不会消失。”晓鸣老师笃定地说。他不认为胶片摄影会被完全淘汰——和传入国内才满20年的数码摄影相比,有百年历史底蕴的胶片摄影怎么可能消失呢?至少在他创建的摄影群和他身边,玩胶片摄影的人不在少数,而且粘性极高。
晓鸣老师在胶片实验室 记者 贺思雨摄
“这张照片没有获奖我是不认可的”“那个135的海鸥是什么型号来着”“135海鸥我有两台:df-1和df300”“记下来记下来”.....三百多人的胶片摄影群里,每天有七八百条发言。这个群没有门槛,也没有什么技术鄙视链——算是一群胶片爱好者抱团取暖的地方。群成员常互相分享照片和相机、讨论拍摄技术或者相约空闲时一起扫街拍照。
大三学生杨浩,接触胶片摄影九个月,是这个群里的成员。
此前,杨浩和他身边的摄影爱好者大多使用数码相机。杨浩萌生了想要尝试一点新的、能够让自己在朋友面前“装”起来的东西的想法,杨浩想到了胶片机。今年二月底,他第一次按下胶片机的快门。
他急切地将照片寄到冲洗店冲洗。等待冲洗的过程吊足了杨浩的胃口,他幻想着一张完美照片出现在自己眼前。然而漫长等待后的结果实在不尽如人意——杨浩想象中画质清晰、构图完美的照片最终并没有出现。
然而他没有被初次失败产生的落差感击退。杨浩发现自己享受这种等待的感觉,不管结果是否如自己预期那般。胶片不能够随心删除,需要非常用心的构图、毫无差错的冲洗,才能拿到一张好照片。
在拿到底片之前,杨浩好像在经历一个繁琐但庄重的仪式,摄影体验感在冲洗底片的时间中拉满。和数码摄影拍到好照片时的瞬时快乐相比,胶片摄影带给杨浩一种延迟的满足。
在晓鸣老师看来,胶片对像杨浩一样生在数码时代的90后、00后来说,是一个足够新奇和标新立异的东西,而对从小接触胶片摄影的成年人而言,更是一种表达情感的精神寄托。
一年前,为了上一门摄影课,晓鸣老师创建了这个胶片摄影交流群。初建立的时候,群里只有他和二三十个学生,而一年后,群里人数翻了十多倍。群成员们还在源源不断地拉自己身边的胶片爱好者进群。现在群里不仅有本校的学生,也有其它高校甚至是社会上的胶片爱好者。
廖少辉接触胶片摄影已六年多,是这个摄影群的一名校外人员。
大学毕业,廖少辉回福建老家闲住。他无意间翻开家中一本七八十年代的老旧相册,一股陈旧气息扑面而来。这些色调特殊、浸润着浓厚时代感的老照片,充斥着和数码相机不同的复古感和真实感,让廖少辉心底生出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受。
六年前的秋天,朋友送给他一台闲置的海鸥相机。胶片机外观复古、皮套精美,虽然镜头有点发霉,但廖少辉并不在意,他只想尽快用手中的机器拍出自己喜欢的照片。晚上回到家,廖少辉找了一个收藏柜,小心翼翼地将相机放进去,用锡纸做了防潮处理,才肯安心入睡。
2016年,辞掉已经从事五年的设计工作,廖少辉决定大胆尝试一把,开始全职摄影。一年后,他成立了一个与胶片摄影有关的公众号,不定期记录自己拍摄的胶片和它们背后的故事。
廖少辉拍的第一卷胶片之一 受访者供图
和廖少辉相比,黄京实在不算一个有分享欲的人,他不喜欢使用社交媒体,上次在某平台更新作品,已经是八年前。
黄京已从事胶片摄影20年,目前经营着一间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摄影工作室。“1987年出生,是一个艺术家。”这是百度百科对他的定义。
2006年高考前夕,黄京跑到美术馆看法国摄影师克劳迪·斯鲁本的摄影展。看惯了摄影论坛里拍荷花、拍人像的照片,展览中的照片和黄京平时接触到的都不一样——黑白的照片没有标准,剥离了外界色彩的干扰,让人单纯去感受某种情绪,充斥着哲学思辨的韵味,一下射进黄京心里。黄京第一次明确感受到专业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的壁垒。
2011年,刚刚毕业的黄京获得了那一年的徕卡·奥斯卡·巴纳克最佳新人奖,凭借十二张自己生活中的随拍。“我拍了一辈子战争图片,见过任何大场面,但看见黄京拍的照片的时候,被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所感动。”一位现场评委说。
他将身边的事物熟悉到了极致,然后通过快门成就艺术品。在他的图片里,没有恢弘的叙事,没有摄影师附加的情感表达,有的只是安静的、黑白色的、黄京眼中的日常。不同的观赏者可以在他的照片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哈姆雷特。
黄京部分作品 图源网络